
第22期
志工經驗交流-日本國際協力事務團(JICA)來台參訪
| 為加強與國際志工組織之志工經驗交流,本會特於經濟部國際合作處協助下邀請日本國際協力事務團(JICA)二本松青年海外協力隊訓練所代所長鈴木秀幸先生來台參訪,期間並分別於十一月廿日及十一月廿二日假本會十五樓會議室舉辦演講,以「JICA運作理念及組織架構簡介暨志工業務執行經驗分享」與「JICA專家來台參訪心得暨對台灣未來志工業務發展方向之建議」為題與所有與會者分享,增進彼此間業務與經驗之交流。 |
 |
|
鈴木秀幸先生詳細地介紹了日本國際協力事務團的發展沿革、組織架構以及現行業務概況。 |
鈴木秀幸先生來台參訪,本會除特別安排他參觀了中正紀念堂與故宮博物院等柔性文化外,並與本會各處室及外交部NGO委員會、青輔會等機構進行面對面深入討論與交流,同時還訪問了相關民間組織如勵馨基金會與慈濟等,希望能藉此增進日本與台灣雙方面的認識,謀求將來彼此合作之機會。
在講座過程中,鈴木先生詳細地介紹了日本國際協力事務團的發展沿革、組織架構以及現行業務概況,使與會者皆對該組織有更深入的認識。日本國際協力事務團(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簡稱JICA)成立於一九七四年,為日本官方對外進行開發援助的單位之一,以提供人力資源的方式來協助開發中國家社會、經濟的進步。JICA目前的業務範疇包含:技術協助、派遣青年海外協力隊(Japan Overseas Cooperation Volunteers,簡稱JOCV)、教育訓練、合作開發、強化社區機能以及急難救助等,而其業務範圍更廣達全球五大洲,在許多蠻荒的角落都可見到該組織的身影。
而在第二場演講中,鈴木先生更針對日本海外協力隊做更深入的介紹。日本海外協力隊(JOCV)為日本參照美國和平工作團模式,於一九六五年所成立的一個青年志工組織,如同本會之海外志工般,每年也都召集有志於從事海外服務的各界青年,在經過基礎訓練後派赴各國從事為期兩年之協助工作。目前每年經由JOCV派遣出國的人數約在1,300多人上下,自一九六五年計畫開始至今更累計了21,506以上的服務人次,派遣的國家數亦達到六十四個之多,服務的層面亦非常廣闊,可說是成效相當卓著的志工執行計畫。
本次演講活動同時對外開放,讓有志深入了解日本志工業務的國內機關團體亦能共同參與,並獲得相當不錯的迴響:國際志工協會台灣分會、富邦慈善基金會、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暨北區志工中心、怡仁愛心基金會以及國家高速電腦中心等已在執行,或有意從事志工工作之機構皆派員參與。藉由與擁有豐富海外志工執行經驗的JICA互相交流,本會也想吸取其成功之經驗,以進一步發展自身之海外志工業務。期望能為國際奉獻更多心力、為志工提供更完備的支持,以及建構出更專業的執行制度,讓台灣的愛心能更廣闊地散佈於世界各地。
美好的成果/駐尼加拉瓜技術團 王增瑞
 |
 |
|
(左圖)駐尼加拉瓜技術團向團長水松在觀摩會上講解陸稻推廣計畫。 |
|
黃金稻穀成就美好未來
「記得剛來到尼加拉瓜時,戚納德加(Chinandega)是一片雜草叢生、雜亂無章的荒郊野外,經過三年來的努力,在所有來賓見證下,看見的是即將豐收的稻穀,農民辛苦工作而有了良好收成,這就是我們技術團付出努力的成果。」這是駐尼加拉瓜技術團向團長在十一月七日陸稻觀摩會播放中華民國國歌之後的片段致詞。看到金黃色的稻穗讓人想起三年前由於本會提供小農貸款計畫的執行,以及技術團稻作小組努力奉獻下,才能有此佳績。今年度從八月份歐碼多里荷(Omar Torrijo) 的水稻推廣觀摩會,延伸至十月份卡爾德納(Cardena)的陸稻,以及眼前十一月份舉辦的戚納德加觀摩會等成果,說明了我們工作的績效與友邦共創美好未來的明證。
預約明年雨季的豐收
首先介紹戚納德加地區的推廣發展情形,三年前的種植戶只有十三位,栽培面積亦僅廿二公頃,每位農民皆抱持著觀望和懷疑的態度來參與,雖然每星期召開會議說明並輔導所有的細節與技術支援,辛勤工作的農民們卻毫無成就感,但在技術團員熱情、不氣餒的鼓勵下,慢慢地化解農民不信任的態度,而有了進展。雖然有部分農民因為經驗不足而無法償還該貸款金額,但辛苦的耕耘、經驗的累積在第二年有了突破性發展,種植面積高達105公頃,產量也從2,307公斤/公頃增加至3,650公斤/公頃,當農民帶著喜悅的笑容歸還貸款時,都相互握手自信的說:「明年雨季來時,我們會更豐收」。今年種植前,向團長曾召開稻作小組年度計畫會議,決定全部稻種的需求將由技術團自營農場生產,而且完全採用技術團新育抗稻熱病的新品種INTA-Malagatoya,如今,美好亮麗的成績在觀摩會的當天表現一覽無遺,不僅種植面積突破243公頃,平均產量也高達4,735公斤/公頃,而且讓當天所有參加的來賓對中華民國技術團刮目相看外,也更顯示我們對尼加拉瓜的所有貢獻。
攜手合作創造亮麗扉頁
技術團稻作小組和尼加拉瓜稻作計畫合作之業務一直在尼加拉瓜擴大發展,我方成果績效已獲得當地政府和私人機構重視。本年十月間,哥倫比亞熱帶稻作研究中心(CIAT)稻作計畫主任李博士(Dr. Lee Calvert)和其技術專家曾拜訪技術團,商議同我方成立中美洲區域性稻作品種改良合作計畫。 尼加拉瓜全國稻米協會(ANAR)、最大的稻米進出口商(AGRICORP和GROUP Z)和歷史悠久的碾米商(PROARROZ)也特來參觀訪問,雖然目前的工作成果已讓人滿意,但我們努力工作的精神並沒有停頓下來,深信還有很多可以發揮的空間及需要改進的地方,期望這累積的經驗和埋頭苦幹的務實作風,對於未來農墾公司專案計畫之經營及管理將可奠定一個良好的基礎。
教 育 e 點 通
人的智慧是一切的根本/教育訓練處 吳台生
參與德國技職教育、職訓專業人員觀摩計畫有感
| 鑒於德國為工業先進國家,其職訓制度具有健全完整架構及深厚豐富內涵,值得學習,我勞委會職訓局於民國八十七年起與德國卡爾德斯堡協會(Carl Duisberg Gesellschaft e v, C.D.G. )合作辦理「技職教育專業人員」計畫,每年派員互訪,進行雙方職業訓練法制、就業服務機制、職業訓練機制、職訓制度運作及相關問題之解決等層面為主題之觀摩研習計畫。本計畫自民國八十七年至今已執行五年,今年九月本會再度應勞委會職訓局之邀,派員與國內其他12個產官學界之學者專家及官員一行15人,共同至德國參與職業訓練專業人員業務觀摩計畫。藉此機會熟悉德國先進之職業訓練制度,以作為本會未來規劃職業訓練計畫之重要參考。 |
 |
 |
|
(左圖)德國卡爾德斯堡協會部門經理Mr. Hubers進行該機構之業務說明。 |
|
多方合作 創造整體效能
此次研習計畫中,我參訪團共計訪問四個政府暨公法人機構,(包括本次負責行程規劃之卡爾德斯堡協會、德國聯邦教育研究部、聯邦職訓教育研究所、慕尼黑勞工局);一個同業公會及一個工會團體;兩所性質不同的職訓中心;三所學校(一所職業學校、兩所科技、工業大學);五家中、大型企業(包括歐洲最大保險集團之德國分公司及聞名全球的賓士汽車慕尼黑分公司)。在結構紮實的實地觀摩行程安排中,也充分突顯出德國職業訓練教育體系完整結合了中央及地方政府、學校與企業三方面之資源與功能所呈現出的整體效能。
以人為本 成就希望工程
為期兩週的技職教育研習過程中,從德西的科隆到德東的柏林,最後一站是前往文化氣息濃厚的慕尼黑,我對C.D.G.所安排德國雙軌制職訓教育計畫行程有一番深刻的體會,可與大家分享。
在德國,國家重視每一個人,認為人是一切基礎、由於人的智慧得以創作未來,並以人為本的出發點與原則,所以無論資質高低均享國家教育資源。另外,在德國約有20%-30%的企業配合政府投入職訓計畫。即使政府對配合政策之企業設有優惠措施予以獎勵或補助,重視團隊工作與社會責任分擔的德國人,在他們的文化中,重視整體及社會責任的精神令我印象深刻。尤其德國雙軌制職訓教育制度強調的重要觀念是「幫學生打開一道門」,此點與本會與友邦進行國際合作,援助開發中國家所傳達「送魚,不如教他們釣魚!」的觀念不謀而合。至此,更印證了「人的智慧是一切的根本」。而如何透過科技進行知識交流、經驗與技術移轉,讓人類的智慧為整個地球村創造更圓滿而富足的生活,將是所有正在進行國際合作援助計畫的已開發國家共同的、也是最終的目的。
造訪歷史 銜接文化軌跡
當然,在緊密的觀摩研習行程外,充分利用各個空檔與週末時間好好一覽德國的文化與風土人情,藉以深入瞭解德國職業訓練體系歷史背景,亦為此行之重要課題。哥德式建築的科隆大教堂、柏林圍牆舊址,都讓我對歷史的遺跡不禁讚嘆;波茨坦之西西里莊園,其屋前保留蘇聯控管柏林時期之紅星,代表德國尊重歷史的中立態度;古蹟的保護及維修亦顯示德國政府尊重文化資產的民族驕傲。而二次世界大戰著名的波茨坦宣言會場,透過英文導覽之解說可想像當年美、英、蘇三國代表杜魯門、邱吉爾、史達林在此會議情形。透過這樣的場景,我彷彿有機會穿越時空對這些令人景仰的時代巨人之因緣際會留下歷史見證。
東西德在不同制度下分隔達四十餘年之久,致使東西德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上有相當的差異,即使兩德統一已逾十載,仍可輕易在柏林看到過去不同政府所留下之痕跡,可見政治制度對一個國家影響之深遠。
| 德國雙軌制教育制度簡介 |
|
源於12世紀手工業師徒培訓制度的德國雙軌制(Dual System)教育制度,以職業訓練為主,由聯邦政府主導制訂法規,工會、企業與研究單位合作參與,規定職業技能,並使學生得以在企業內學習;另以職業教育為輔,依據職訓需求,設計通識與專業課程,提供學生學習一般數理、語文與專業理論之需。學徒取得證書後,以就業為優先選擇。有別於我國技職教育以學校教育為主,學生畢業後,多數以升學為優先考慮。 |
| 卡爾德斯堡協會組織簡介 |
| 卡爾德斯堡協會(Carl Duisberg Gesellschaft e v, C.D.G.)係一接受德國聯邦政府及其國內外企業團體經費補助及委辦業務之非營利性法人機構。重點業務為德國職業教育與進階訓練等人力資源發展議題之國際合作交流計畫之執行。其機構的主要業務之一為以德國之職業訓練經驗為基礎,提供開發中國家技術協助而達促進其國際競爭力、改善其生活品質之目的,並最終以達全球人力之發展與進步。該機構將於2002年10 月與該國另一司職國際合作、援助開發中國家業務之法人組織-德國國際發展基金OSE(THE German Foundation fro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合併改組為Society for International Further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InWent。據CDG表示合併之後該組織與我國的交流互訪計畫將維持原貌,由於新組織InWent將概括承接OSE之業務,屆時其所掌業務將更形多元多樣。 |
改變世界的台灣希望工程(上)
| 本文出自於《台灣心、世界情-愛在他鄉的八個動人篇章》,這是一本敘述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故事的書,同時紀錄著「台灣陪著世界一起走」的足跡─在戰後世界發展的歷程,特別是第三世界低度開發國家掙扎成長的過程裡,台灣始終向需要扶持的國家伸出溫暖的手,一直沒有缺席。 這本書,或者更精確的說,記錄著「世界邊緣的台灣人」的故事,他們以自己血汗為筆,以友邦大地為紙,寫就另一篇台灣歷史,也寫就一篇篇超越國界、種族、時間的至情、至真、至善,宛若天使走過人間的美好傳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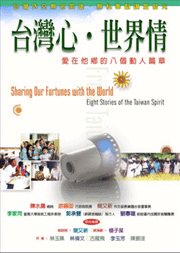 |
「無論是誰都會同意,發展與降低貧窮的最重要關鍵,就是教育。」世界銀行總裁James D. Wolfensohn說。使世界免於貧窮之苦,一直是世界銀行的夢想;而教育,始終是世界銀行致力於降低貧窮的任務核心。也就是說,幫助開發中以及貧窮國家來投資他們自己的人民,才能促使這些國家有能力邁向永續經濟成長之路。
在二○○○年,來自一百八十個國家的代表齊聚在西非塞內加爾的首都達卡,他們在這個「世界教育論壇」上為改善全球教育一起做出承諾。雖然台灣不在聯合國會員國之內,未能躬逢其盛,但台灣的努力不曾缺席。
四十年來,台灣經驗不只是台灣永續發展的基礎,也是促進世界發展的重要活力之一;與世界分享台灣經驗,共同追求世界成長與福祉,也成為台灣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推動國際合作發展的核心。而教育,是分享與落實台灣經驗影響最為深遠的管道,從過去辦理短期研習訓練、與國際組織共同合作人力資源培訓計畫,到如今與國內大學如屏東科技大學、政治大學、台灣大學合作,提供培養友邦高等技術人員的專案計畫,一步一履為培養人力資源、降低世界貧窮做出貢獻。
台灣雖小,但可以創造出經濟奇蹟;一九九七年才成立的屏東科技大學熱帶農業研究所,在世界版圖上難引人注目,但一項改變世界、可以帶來綠色革命的希望工程,在熱農所與國合會攜手合作下,悄然展開。
屏科大熱農所啟動綠色革命
「一切從零開始,」屏東科技大學副校長賴博永提起當年辭掉夏威夷大學熱帶農業及人力資源研究學院助理院長,返回台灣接下熱農所所長一職的創業唯艱,如此輕輕帶過。開辦熱帶農業所,是屏科大要走進世界、邁向國際化的重要里程,因此培養高等農業技術的國際人才,成為賴博永的重要目標之一。
然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賴博永找上老友、國合會顧問謝順景博士,正好國合會也在尋覓國內學術機構作為培訓友邦技術人才的教育夥伴,就在如此因緣際會之下,台灣跨出了國際合作發展的教育訓練新出路,屏科大也因而成為國內第一個提供英文教學、培訓外籍人士的碩士學程學校。
短短五年,隨著友邦畢業生的返國服務,屏科大熱農所的名聲漸揚,愈來愈多的友邦推薦有潛力的人才參加甄選。目前熱農所博、碩士班外籍學生一共有二十七位,分別來自十七個國家,小小的屏東縣內埔鄉,也因為是熱農所的所在地,成為外國學生國籍最多的小鎮,與世界關連密切。
把農業產銷技術帶回甘比亞
「我想來了解有『亞洲之虎』美稱的台灣,如何創造經濟奇蹟。」來自西非甘比亞共和國(Republic of Gambia)的范方定(Fafanding S. Faiajo)說。一九九三到一九九七年間,他在馬來西亞念大學,就已經聽聞很多有關台灣令人驚奇的發展成就。三、四十年前的臺灣是一個開發中國家,如今已幾乎成為已開發國家。雖然歐美已開發工業國的發展經驗也有許多值得學習與借鏡的地方,但相較之下,臺灣經驗很Fresh,也可能比較適合目前正在奮起直追想晉身開發中國家的甘比亞。「一個新興的已開發國家,是開發中國家致力經濟發展最好的學習典範。」這也是他來台灣屏東科技大學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當范方定從政府農業部知道台灣國合會提供碩士獎學金,他就報名申請,最後在至少七位競爭者的角逐中脫穎而出。他在臺灣主修的是農業企業管理,他認為,甘比亞如果要促進經濟發展,勢必要把農民從傳統的交易帶到現代企業化的管理,也就是要知道如何在全球市場經濟中生存的方式。在甘比亞,農民缺乏世界經濟的「資訊」,沒有資訊,甘國農業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前行。
甘比亞西濱大西洋,面積大約是台灣的三分之二,人口只有一百多萬,國民所得每人每天平均不到二塊美金。一九九四年上台的賈梅總統銳意圖治,擘劃遠景希望在二○二○年使甘比亞成為中等收入國家;而「台灣經驗」將有助於努力躍升的甘比亞。台灣當年進行土地改革,以農業發展工業的經驗,令范方定印象深刻,尤其是農會組織的發展,在政府農業部門極為有限的官僚人力,與為數眾多分布廣大的農民之間,扮演很好的政策宣導與農業技術推廣的連結橋樑。來台年餘,他說:「我學到的,遠比預期的還要多。
提起Dr. Lai(賴博永),范方定直說從他那裡獲得很多幫助,也使他在台灣的生活經驗豐富起來。除了專業知識上的獲益,賴博永總會提醒這些隻身在台的大孩子們各種生活或專業知識上須注意的事。今年六月已通過碩士學位考試的范方定,雖然離回家的日子很近了,但一談到「回家」,語氣仍掩不住急切。「我要把我所學的,為我國家的發展做出貢獻,」他還說他會想念在台灣、在屏科大熱農所的種種,而且他永遠不會忘記台灣這個國家,「因為台灣經驗已經成為我人生的一部份。」
我在布國的快樂泉源/駐布吉納法索技術團役男 吳國銘
| 遠在西非內陸的布吉納法索雖然和台灣有著截然不同的人文風俗習慣、語言及氣候,然而,從第一屆外交替代役男吳國銘的眼裡,卻發現到只有身在布國才能擁有的快樂與溫暖,讓他看見另一個有讚美、有感恩的化外世界。 |
 |
 |
|
(左圖)我駐布國陶大使文隆與賈秘書視察技術團第永格列分團陸稻墾區開墾情形。 |
|
「接受」從我真正認識布吉納法索那天算起
身為第一屆外交替代役的我,來到這個氣候炎熱的西非內陸國-布吉納法索服役已經剛好一個年頭了,雖然這裡的人文風俗習慣、語言、氣候等與台灣有著極大的不同,甚至還有無所不在的瘧蚊及沙塵暴的威脅,瘧疾可以讓人三天吃不下飯,什麼事都做不了,甚至高燒不退,頭痛欲裂,而沙塵暴可以阻擋眼前二百公尺的任何景物,連呼吸都可以嗅到沙土的味道,而這裡夏季高達攝氏45度的高溫可以讓車子吹出來的冷氣到你身上時已經變常溫了,說真的,這是很難得的一個體驗,然而現在的我已經習慣了這裡的所有,也對這裡有一定程度的瞭解。而在這裡看似極為規律且枯燥乏味的工作與生活,每天除了工作、用餐外,晚上就是待在團部裡面,除了上法文課外就是自己看看書,而假日的休閒活動除了打網球外沒有其他,可以說再規律也不過的生活,套一句軍中的行話,就像是每個週末都是「在營休假」般,團部的駐地是鄉下,根本也沒有地方可以去,剛開始抵達時真的不太習慣,然而仔細觀察後,仍可以發現許多快樂的地方,尤其是越深入瞭解這裡的農民及工人,越可以發現這裡可愛的一面。
「幫助」從肢體語言中透露無疑
早晨六點的鬧鐘在我耳邊響起,起床盥洗後,前往餐廳用餐,六點半跟著技術團水利專家及技師前往工地,又是一天的開始。而每天的工作就是我最快樂的時候,在前往工地的路上,看到一望無際綠油油的水稻田讓心情都輕鬆起來,好像置身在自己的故鄉一樣,而當我技術團專家看到水稻顏色漸黃需要施肥、稻田太乾需要灌溉或是雜草太多應該除草時,他會用流利的法語通知農民,然而這裡農民接受過教育的不多,有時候李專家會用人類最傳統的語言「肢體語言」告訴農民,而農民看到我們都非常的高興,因為他們知道我們是來幫助他們的,每當看到農民純真的笑容就是我們最快樂的時候,當然也會有懶惰的農民,不僅所分配的一公頃沒有插完秧且插完秧的也沒好好的照顧,這時就會叫農民主席去通知他們儘快插秧且記得灌水及施肥,而如果他們還是依然故我的話,李亞倫專家就會叫農民主席去他家把他叫來,然後先問他為何已經授田那麼久了卻沒有插完秧或是為何水稻沒有好好的照顧,而一般來說他們都會有說不完的理由,什麼他的太太叔叔伯伯哥哥生病了啦、他的親人過世了、沒有水啦、土壤不好啦….等,然而其實瞭解他們的話就會知道這些都是藉口,這時專家就會用開玩笑的口吻罵他們說:「懶惰就是懶惰啦!一堆理由,即使有事為何已經那麼久了卻還沒有插秧?如果真的是沒有水的話,我們每天都會經過可以告訴我們啊,我看你根本就沒有來田裡對吧!?」而此時農民就會笑笑的露出尷尬的表情,然後李專家會給他三天的期限必須將沒整好的地整好並插完秧,如果超過期限的話就威脅會收回他們的田地,因為後面有許多的布國人民等著排隊授田,這時他們就會露出非常害怕的神情,並一直道歉請求不要收回他們的田地。隔天當我們再去巡察時就會看到農民帶著全家大小、親戚朋友全數近三十個人努力的在田裡工作,此時專家就會笑笑的告訴我「你看,稍微警告一下,他們明天就全部完成了。」而我除了露出會心的一笑外,更是佩服他管理農民的方法。
「值得」在布國的豐收及感恩中湧出
當然大多數的農民都是很認真勤勞的,所以每當他們高興的跑來告訴我們這一期水稻他又豐收時,有時他們會帶著羊或雞送給我們,向我們表達感謝之意,並說到因為有技術團的幫助,讓他們從一無所有到現在有飯可以吃、小孩有書可以唸、有腳踏車甚至機車可以代步,真是大大改善了他們的生活,雖然一隻羊或幾隻雞對我們來說不是什麼大禮物,但是卻足以代表他們內心最真誠的謝意,畢竟一隻羊或幾隻雞可以讓他們一家過整整一個禮拜,每當我看到他們送的禮物及聽到他們所表達的謝意時,心裡不知有多麼高興,高興的不是那隻羊或那幾隻雞,而是他們有了大豐收及他們的感恩,雖然我只是身為駐團助理也沒提供他們多大或了不起的幫助,但是身為我國駐外的一員也感到與有榮焉,有些農民甚至說將要求布國政府頒發給專家技師們布國的身份證,因為他們已經把我們當成是布國的人了,每當聽到這些話時,專家就跟我說不管他在這裡多麼的辛苦都值得,而此時的我已經感動的無法言語。
「讚美」在各界的迴響中流傳
而就在前陣子法國的知名電視台France2來到分團所開墾的陸稻墾區採訪,而後在晚間的黃金時段晚間新聞做了相當的報導,而此段報導就緊接報導在南非所舉辦的世界永續發展會議之後,內容提到就在世界各國在為非洲糧食問題作討論時,有一個亞洲的中華民國台灣從卅年前的姑河墾區到現在的巴格雷水稻墾區及第永格列陸稻墾區,已經默默的在非洲布吉納法索開墾了數千公頃的稻田,並大大的解決布國糧食缺乏的問題,同時也改善了數以千計的布國人民的生活,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裡面有一段訪問當地農民的採訪,農民開心的提到他們感謝上天的降雨及中華民國的幫助讓他們有田可以耕種才有糧食可以維持生計,但是「Dieu n'est pas ici , ce sont les chinois qui sont la」意思為「上帝不在這裡,而是中國人在這裡幫助我們」,當我看到這段報導時,就像是之前專家說的一樣,所有的辛苦都已拋在腦後,而此時,讓我想到阮耀鋒弟兄在ICDF第十九期電子報裡面提到的「與其埋怨玫瑰的多刺,不如去讚賞那多刺中那朵美麗的玫瑰花呢?」多刺的是布國的氣候環境惡劣與疾病的叢生,而那朵玫瑰花就靠我們去慢慢發覺與欣賞。
部落的小小學/駐哥斯大黎加志工 張幸運
| 藉由部落醫療的接觸,讓志工幸運對Alto Cuen和San Jose Cabeca兩個部落孩童失學的問題有一份責任。對她來說,目前剛剛才開始進行辦學中的小小學,是她對印地安保留區部落的牽掛,也是讓她能夠克服外在不便利生存環境的動力,因為和為部落創造未來的小學與孩童可以就學相比之下,所有過程的辛苦與疲累,都值得了。 |
 |
 |
| (左圖)跋山涉水來到深山裡的部落。 | (右圖)擠在一個屋簷下的大家族。 |
今年部落的醫療年度計畫裡,最特別的事是前進最深山裡的部落:Aalto Cuen和San Jose Cabecar。首先需至每週一、二巡迴醫療的部落Sepecue(由小女子居住的BriBri部落需搭半小時的救護車,接著轉一小時的獨木舟之後步行一個半至兩個小時才能到達Sepecue),由Sepecue至Alto Cuen需步行八小時,無其他交通工具。當地的村長告訴我,在我們之前也是六年前有醫生像我們一樣徒步上部落去醫療;最近一次則是六個月前也就是年初時,因為急診所以派直昇機到那裡去,不過只停留短短的半小時,曇花一現的結果並無太大幫助。而這一次,終於讓他們盼到了!
我們由Sepecue一路前進,沿途泥濘不堪,穿著雨鞋的我幾次鞋子深陷泥沼,必須手腳並用才得以脫身;在經過湍急的河流時水深至腰,滂沱的大雨更是無情的打在身上,雖然心生恐懼也只能緊跟著嚮導咬著牙奮力過河。就這樣好不容易才到達Alto Cuen,而小女子則勇奪女子組第一名!我們住在當地人的家裡,最令人不敢相信的是他們竟有十七個小孩!
雖然我們都已帶了一些乾糧和水,他們卻熱情的為我們準備了一些食物:水煮的pijivalle,長的像小檳榔吃起來則像地瓜,而這竟是他們一家人每天的主食。夜晚我們則睡在由一片一片樹皮鋪作地板的穀倉,廁所和大多數部落一樣是挖個大坑,用幾片木板圍起,連門都沒有直接面對著大自然;而全身髒兮兮、汗水黏糊糊的我們則在河裡洗澡,先穿好雨衣、脫下髒衣服、洗頭洗澡、再穿起衣服就大功告成。那一次其他兩位志工靖雯和美玲也與我一起上山體驗山裡的生活,一路上互相扶持、鼓勵,夜晚則擠在一起取暖、分享食物,平常只有我一個人和醫療隊上山出診,而這一次則讓我感受有同伴的感覺真好。
本來預計一週的醫療,但在第三天,因為我們黑人護士的父親去世,消息由腳夫一路上傳,一接到消息醫生馬上下令集體回航,為這次的醫療留下了淡淡的遺憾。
由Alto Cuen回來後,我心裡對這個部落一直有個牽掛,常常在想我可以為他們做什麼呢?這個最內地、原始的部落,甚至當地國家的人都不願意去觸及的地方,有許多的村民連哥國的國語西班牙文都不會說,還是只保留他們原來的族語,看醫生時都需要有人為我們雙方翻譯,這看似被遺忘的世界角落,我可以為他們做些什麼呢?我不斷思考著。
八月回來後,不斷思考著Alto Cuen的事。也許是從上帝而來的感動吧!也許我們可以為他們蓋所小小的學校的構想從心中萌芽。
哥國從一九三○年左右小學教育即開始普及,但是印地安保留區裡的部落仍有些孩子沒有書唸。Alto Cuen和San Jose Cabeca兩個部落相距約一小時腳程(不是我的腳程而是印地安腳程哩),但到最近有小學的部落卻要八小時腳程,因此,所有的孩子都是失學的;而這兩個村落共將近有四八○人,因此一個小小學也許對他們是有所助益。
首先,我探訪了幾個常出診部落裡的小學,和學生、老師談他們上課的情形,之後和Sepecue村子(最靠近Alto Cuen有學校的部落)裡的人探詢這件事的可能性以及Alto Cuen村民的意願,經過許多評估和討論後認為這事的可行性頗高;而最重要的是,每個Alto Cuen的村民一聽到辦學的事,每個人都很高興並殷切的期望著,而這也就成了我動力的來源。
目前初步的規劃中,除了幫助他們學習西班牙文和一些知識外,最重要的事幫助他們將印地安人原有的文化透過教育留存下來。我看過幾本無論是人類學家、旅行者或考古學家在接觸過印地安人之後都有相同的結論:人們常常把自認為必要的價值塞給別人,並強迫他們放棄原有的。而這不正是殖民主義的寫實嗎?還記得有一個故事,一個救援團體到了某國家後看到當地的人都涉水過河,覺得他們很可憐,於是在大河上蓋了一座橋,到了落成典禮當天來了許多媒體爭相報導,搶著拍下第一位過橋者的喜悅,終於來了一個村民,卻在眾目睽睽下仍涉水過河,一位記者問他:你難道不知道可以從橋上過嗎?村民冷冷的回答:為什麼你們這些外來者總是做你們認為「我們需要」的事呢?你們破壞了我們祖先原有的環境,而這並不是我們所要的!!當場一片悄然無聲。因此,在我理想中的部落小小學裡,BriBri語(BriBri族母語)是必須教給孩子們的,而他們的文化也不是我們應該去改變的。
辦學的師資來源是一個迫切的需要,詢訪很久後終於找到有一個村民同時懂西班牙文和BriBri語,同時他也曾就學至中學三年級,後來因家裡無法提供經濟支援下不得不輟學,但是對我們的小小學而言,是足夠了。之前我還在煩惱,小學六個年級,我到哪裡找六個老師呀?又要會說二種語言;又要願意深入到這個部落,真是很困難哩!但我的印地安媽媽說,只要一個就夠了呀!因為大家通通沒上過學,所以都是相同程度---「一年級」,啊!哈!對呀!於是師資的問題解決了。
蓋學校方面,有一戶人家願意把地捐出來,而在建築材料上則採用天然建材(木頭),小女子和當地村民討論的結果,初估約需十萬colones(約台幣一萬元),你相信嗎?一萬塊錢耶!就可以蓋一個小小學,替二個村子裡的人圓半世紀的夢!這令我很興奮。
十一月,小女子和另一位志工Irene和村子裡的人約好去看地,在這之前Irene就開始了她的準備工作:常常和我一起往部落跑,訓練體力。終於到了上山看地的日子,由於鄰近加勒比海,山區終年雲雨繚繞山路亦泥濘難行,雨鞋就成了上山的必需品。有鑑於第一次到Alto Cuen時所有衣物被雨淋濕外,行經湍急的河水更是全身濕透行李也全部泡水,因此我們仔細的把所有東西都用塑膠袋多包了幾層,Irene聽到小女子形容河水的湍急和水流之深,讓她不禁想到八掌溪事件。
記得第一次到Alto Cuen行程是三天兩夜,而這次為了配合醫療隊來回,所以我們必須縮減為兩天一夜,這對我們體力和耐力的負荷不外是一個很大的考驗。其中有幾次,小女子爬到沒力,體能上實在很想放棄(可是沒辦法放棄,路程只能前進不能後退)一路上都靠著對辦學的負擔和意志力支撐著,一邊默默禱告和低唱詩歌,終於在上帝和嚮導的幫助下成功抵達。
我和Irene一到當地人家的時候,全身幾乎癱瘓,小女子一路上受缺水之苦(喝掉2000c.c.還不夠),而Irene更因膝蓋舊傷復發疼痛不已,可是原本已癱在椅子上不能動彈的她,一聽到嚮導拿甘蔗吃,馬上爬起來要一根,讓我看了傻眼,原來她是又累又餓,所以到最後才走不動。趁天色未全黑,我們趕緊到河邊洗澡除去一身難聞的汗臭,河邊洗澡嘛!還是用老方法穿著雨衣洗!
晚上和部落裡的人開會,討論蓋教室、教學、資源和奉獻,我想這是除了自己出去玩外,第一次覺得西文可以講的這麼溜!開會時,長老說的第一句話是:你對我們而言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當下心裡真是百感交集,憑心而言,小女子不在乎別人怎麼看Esperanza(張幸運之西文名)這個人,因為,也許二年後誰還記得你長什麼樣子?心裡在乎的卻是做的這些事情對他們到底有沒有益處?只有上帝知道答案,而我只能盡我的努力去做就是了。
隔天,我們一口氣趕下山,總計廿二小時之內我們有十二小時是在走路,第三天小女子四肢幾乎動彈不得。不過,終於一切事情塵埃落定,下星期就開始動工了,這是我最喜悅的事,也盼不是為了人的驕傲而是為神的喜悅。
~期待我們的部落小小學~(12月後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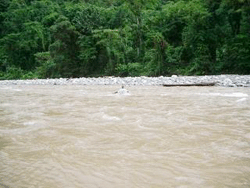 |
 |
|
(左圖)前進最深山裡的部落之前,還得先接受穿越急流的考驗。 |
|
- 更新日期: 2022/05/25
- 點閱次數:896
